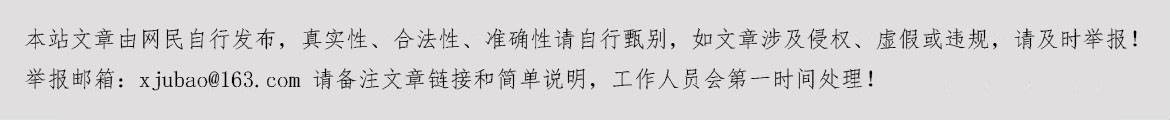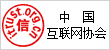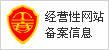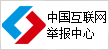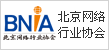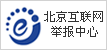暴跌99%!被顾客骂惨!火了20年的呷哺,是如何作死的?
2021-05-04 16:22:02
若要问你吃火锅的第一选择,你可能会想起谁?
现在应该很多人会说是海底捞,但放到几年前,这个答案却很可能是呷哺呷哺。
这个来自台湾的一人小锅曾经是许多学生党、北漂族们的火锅心头好,在热气腾腾的冬天,吃一顿有肉有菜有经典麻酱的小火锅,价格不过是30-40元。
然而这些年来,呷哺呷哺却不再亲民,吃一顿往往要60-70元,让人越来越吃不起了。
有网友评论:“呷哺呷哺就是丫鬟的身份、公主的要求,娶回家了脾气还死差。”
也就是说呷哺本来作为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却硬要往高端路线上靠,结果装B不成,反倒把自己的性价比优势搞没了,价格上涨,但产品和服务水平都变差了。
随着消费者的口碑持续恶化,呷哺呷哺的业绩也是接连暴跌,其净利润从2018年以来,已经出现连续三年下滑的状态。
2018-2020年,呷哺呷哺的净利润分别为4.62亿元、2.88亿元、183.70万元。
叠加疫情冲击,呷哺呷哺的业绩更是惨不忍睹,其去年实现收入54.55亿元,同比减少9.5%;公司拥有人应占年内利润总额为183.7万元,同比减少99.4%;2020年,集团新开张91间呷哺呷哺餐厅及38间湊湊餐厅。
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呷哺呷哺的股价如今只有132亿,相比比它晚了好几年创立的“后浪”海底捞,后者是指如今已经高达2761亿(4月29日数据),相当于个20呷哺,简直是被“后浪”拍死在了沙滩上。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呷哺呷哺究竟经历了什么?它是如何把自己步步作死的?
01
疫情期间的新网红:有事找民警,吃饭找呷哺
从默默无闻到一夜爆红,再到如今的日薄西山,呷哺呷哺经历了两个起落轮回。不知是命定还是巧合,呷哺的“起”是因为非典疫情;而它的“落”是在新冠疫情中大大加剧。
呷哺呷哺的创立者名叫贺光启,这名台湾商人出生于一个珠宝世家,家里资产高达5亿,但他子承父业之后,仅仅一年时间,就差点把家产败光了,气的老父亲差点跳楼寻了短见。经过打击之后贺光启决定发奋图强,把亏掉的家底赚回来。
这时,他注意到了日本流行的一人锅在中国台湾遍地开花,这种火锅干净、快速、方便,而且标准化程度极高,非常有希望做成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品牌。
于是,商业嗅觉敏锐的贺光启将这种模式引起了大陆,“呷哺呷哺”由此诞生,并于1998年在北京西单开了第一家店。
不过刚开始,习惯了吃围炉火锅、铜锅涮肉的老北京人们,对呷哺这种新模式并不感冒。呷哺的生意极其冷淡,一天也卖不出三锅。
转机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疫情让人们发现了一人锅安全、卫生的特性,加之后疫情时代“单身经济”开始兴起,呷哺得到了广大消费者们的认同;再加上呷哺主打性价比路线,小料4元一位,底料2元,肥牛套餐才46元,人均消费不到50就能吃到撑,这让它尤其受到了北漂族、学生党等价格敏感用户的青睐。
“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下,呷哺开始爆发式增长,所有呷哺餐厅的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其翻台率达到一天7次,几乎是火锅行业之最。
那时,呷哺呷哺的老板贺光启常常用一句玩笑话,来形容呷哺呷哺在北京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北京的民警驻点有315家,而呷哺遍及北京各区就有276家门店,几乎可以说是‘有事找民警,吃饭找呷哺’。”
很快,呷哺在北京的门店数量就超越麦当劳、吉野家,仅次于肯德基。贺光启还定下了“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比肯德基多一个店面”的雄心壮志,立志成为中国最大的速食品牌。
不过,呷哺的战场绝不止一个帝都,依托北京大本营,呷哺模式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并于2014年在香港主板上市,成为快食火锅第一股,彼时公司的餐厅总数达到420多家。
上市后,公司更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其发行价从4.7港元一路涨到17.5港元,上涨了3倍多;营收也是增势迅猛,2014-2017年营收分别为22.02亿元、24.25亿元、27.58亿元和36.6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41亿元、2.63亿元、3.68亿元和4.20亿元。
呷哺迎来巅峰时刻,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贺光启在接受采访时,放言呷哺要扩张至4000家,拿下全国火锅市场。
02
丫鬟的命,却得了公主的病?
总的来看,呷哺之所以能迎来爆发式增长,表面来看是因为疫情的催化;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性价比优势。
但是,贺光启却发现,这种模式赚起钱来,实在是太慢了。与汉堡薯条可乐等食品品类可以拿了就走、就算堂食也可以快速吃完不同,火锅几乎只能堂食,而且食用时间相对较长。
一天7次的翻台率几乎很难突破,但呷哺的人均消费仅为30多元,因此呷哺的坪效是很低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在单店盈利能力恒定的情况下,把数量提上来,多开店成为了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呷哺的扩张速度之猛,令业内咋舌。2016年,呷哺还只有553间门店,到2019年仅3年时间,就新开402间门店。
但是餐饮作为一门重资产的生意,店铺猛增对呷哺供应链能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订货、存货周转、配送、人员管理等都需要大量投入,这让贺光启头痛不已。
这时,“后浪”海底捞开始崛起。在行业都在纷纷学习海底捞的服务模式之时,贺光启却领悟到了海底捞的赚钱效应。
2017年6月,贺光启在上海宣布呷哺从“快餐”转型“轻正餐”,效法海底捞,走高端化(高价格)的路子。
升级后的呷哺一盘肉要30元~40元,一杯奶茶要20元~28元,2020年年报显示,呷哺呷哺在一线城市的人均消费已经达到65.2元。
在大众点评等软件,人均价格更是升高到了70元-80元,部分一线城市门店消费金额甚至可以达到90-100元。
当然,为了给消费者们一些涨价的理由,餐厅装修也进行了升级,大幅减少了一人吧台式座位,增加二人、四人桌位,产品线增加,由包装小料变为小料台,增加台式茶铺,餐厅环境变为新中式禅风等等。
但消费者们,对呷哺的改变并不买账。价格越来越贵,但是服务越来越差,菜品越来越难吃,而且快餐式的小火锅也变得越来越慢,有很多网友吐槽,等了40分钟,锅底都没上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因素导致,呷哺的升级意味着服务难度的增加。此前顾客围着服务员,服务员可以快速高频达到用户。
但座位一旦分开,就变成了服务员围着散座的用户跑,服务难度自然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客单价提高了的呷哺,在形式上越像海底捞,越会加大用户在主观层面对服务的期待,但服务能力又跟不上来,自然会进一步影响体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呷哺的这条路一开始就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它“性价比”的印象已经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贸然走高价路线会让消费者产生“不值”之感,“有的时候就想吃个便宜的、味道过得去的火锅,真的不太需要这么多‘附加值’。”
“如果有这钱,我为啥不去吃其他高端一点的火锅品牌呢?”
这是商业社会的普遍规律,如果换作是小米的产品,突然要收苹果的价格,那么消费者也肯定接受不了。
消费者们的“用脚投票”,从数据上也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
2017—2019年,呷哺呷哺客单价分别为48.4元、53.3元、55.8元,翻台率却在不断下降,分别为3.3、2.8、2.6.2020年,呷哺呷哺客单价上升至62.3元,翻台率为2.3;2020年上半年,因受疫情影响,翻台率一度低至1.8。
03
顾客和企业,谁才是上帝?
大概是意识到了呷哺自己提价的尴尬,贺光启又推出了新的高档品牌——2016年,呷哺推出高端品牌湊湊,客单价与海底捞相仿。
但是消费者们普遍反映,湊湊仿佛只是为了“高端化”而“高端化”,其产品服务的创新,毫无特色可言。
首先从产品来看,高端品牌必须要有独特的创新产品,以与其他品牌形成区隔,如8号火锅的灯影鱼片、西班牙橡木果黑猪颈肉、黑鸡枞菌、老虎斑、鲍鱼锅底、鸭嘴鲟等。但看看湊湊的主打产品,包括大红袍奶茶、风味鸭肠、海鲜棒棒糖、雪花牛肉粒等,这些所谓的招牌特色创新产品满满的工业标准风,既没有产品壁垒,也没有实质上的新意。
其次,从场景体验来看,湊湊基本上就是照搬了典型的日系风格,缺乏高端品牌所需的设计感、美学、独特性、质感;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湊湊门店的奶茶在堂食端居然用的还是专供外卖的一次性杯。
最后,从用户评价来看,湊湊多数门店在点评也差评甚多,但是差评却无人跟踪、无人回复、无人改进。
湊湊似乎是觉得,自己看不到,这些问题就不存在?
其实这种对于消费者的慢待、冷漠,从呷哺的内部经营管理就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
据一位呷哺员工透露,呷哺的“创新”,都是脱离了消费者的“跑脑袋”决定。
“产品线完全脱离市场需求,呷哺从一开始到今天推出的所有东西几乎就是在自嗨,几个人窝在办公室拍脑门,完全没有真正做过市场调查,更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市场调查的方法与核心是什么。”
似乎过去的成功经验让呷哺有了这样一种错觉,幻想他们是上帝,无论呷哺给什么,顾客都会为此买单。
但消费者又不是傻子,你如何待我,我就如何待你。所以尽管重新“定义”了湊湊的翻台率,也就是将每一笔与堂食顾客平均消费对等金额的外卖订单,都被视为堂食顾客的一次翻台。
但是就算有外卖数据注水,2020年,湊湊餐厅翻台率依然从2019年的2.9降低至2.5,尤其是在上半年,其翻台率甚至只有1.9。
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你那段时间在湊湊门店进行消费,那么你很可能就是你那一桌在一天内所接待的唯一顾客。
对比起海底捞常年为5,疫情期间也有3.5的翻台率,湊湊的尴尬一看便知。
04
当经营企业变成一场数字游戏
事实上,呷哺从曾经的风光无限,到后来的差评不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已经脱离了一家火锅企业需要做好产品、做好服务的本分,而是陷入了一个盲目追求指标、玩数字游戏的怪圈。
呷哺高管们都在看数字,但却根本不理解这些数字里面和背后的意义。为了完成这些数字,员工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欺骗性”的手段——
比如说,新品茶饮销售数量不好看怎么办?
没关系,可以把其他非茶饮全部下线,硬逼顾客点茶饮,或者原价20多元的茶饮按8元卖。
这样一来,数量倒是提上来了,但是结果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体验,还影响了企业的利润和品牌力。
更夸张的是,对于一些利润比较薄的产品,即使非常受到消费者欢迎,例如以前畅销的精品肥牛、新西兰牛肉等,后来也给直接下架了。
呷哺丝毫没有意识到,失去了消费者的数字,不过只是一个个空壳而已。
可以预见的是,只忙着追求数字,忽视了真正产品服务的核心的企业,最终必将连数字也会失去。
火锅是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目前全国在营业的火锅门店数为47.1万家,没有品牌特色、缺乏产品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怎么可能长久立足?拥有足够选择权的消费者,抛弃一家企业实在太容易了。
不过,关于这一点,或许已经没人在意了,管理层和投资者们要么套现,要么弃船。
今年1月、4月,呷哺呷哺CEO赵怡两度减持,套现合计约3000万港元;3月中旬,在呷哺呷哺发布2020年财报前半个月,大摩、高瓴资本均以接近清仓力度减持;近日,旗下湊湊CEO张振纬也已辞任。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基业长青的企业,没有永远不败的商业模式。
热闹过后,曲终人散,留给这世界的,徒有一声叹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