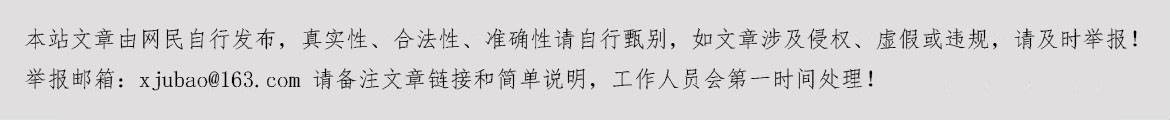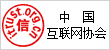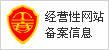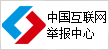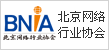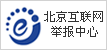人生,就是一具皮囊包裹一颗心的羁旅
2021-05-09 14:58:00
蔡崇达的《皮囊》再次阅读,,感触又有诸多不同,在一个气温如同夏天的春天午后,走进那些熟悉又些许陌生的故事,再次思考生与死,皮囊与灵魂,一具具皮囊包裹着一颗颗心行走在这世间,正如李敬泽在《皮囊》书序中所道:人生,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
一直纳闷一位80后的年轻人怎么就对人生有这么犀利的认知?怎么就能用这种笔触缓缓剥离众生的皮囊?清晰呈现游走在世间的各式灵魂......
带着问题再来看《皮囊》这本书,不再如第一次般阅读故事注重情节,更多的是关注作者本身的成长轨迹,那个拿着木棍走出小镇的少年是如何伴着登山杖踏访名山?再次细嚼《皮囊》,结合他所有的经历,就明白了现在的蔡崇达,如何应用采访生涯所学会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的方法去抵达一个人,内心哪里痛就摁哪里,把哪里解剖开,写出来......
16岁获得全国创新作文大赛一等奖;18岁考入泉州师院,大三时破格被某媒体聘为深度新闻周刊主编;22岁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生活》月刊《周末画报》工作并任主编,曾担纲央视汶川地震专题纪录片策划及撰稿工作,并与白岩松合作《岩松看美国》系列节目;27岁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中国新闻业的最佳特稿作者,其新闻作品曾获《南方周末》年度致辞敬最佳报道奖、亚洲出版协会特别报道大奖,以及德国《德意志报》颁发的中国年度特稿奖。
正如蔡崇达所说,《皮囊》是为了找到父亲,那位因中风而离开人世的父亲,追忆生前受困于皮囊努力挣扎的父亲,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境况,迫使自己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他用写作的方式抒发自己内心最强烈的内疚、自责和无能为力的无奈,唯独没有抱怨——残疾的皮囊是凡人多么难以驾驭的重负,对皮囊的妥协,是一颗心最绝望的呐喊。
蔡崇达没有写自己在家庭困难时个人的艰辛,但我们在书中的故事中看到了他未成年的担当,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儿子,他扛起了自己的责任并迅速成长强大起来,与家庭成员一起撑起了家。
在蔡崇达很小的时候,他的阿太(外婆的妈妈)就对他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潜移默化的观念根植于心,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他多方面见证了阿太对于皮囊的态度与做法,他听到别人说起阿太年轻时如何将不会游泳的亲生孩子再三抛到河里;他看到阿太用刀砍到手指,家人慌乱一团自己若无其事的淡定;看到了92岁高龄裹着小脚的老人坚持自己从乡下走到镇上;他看到摔断脚动不了的阿太叫嚷着自己被困住了动不了啦......
所以阿太心中的黑狗达,在阿太去世时记住了“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方便多了”,蔡崇达写下了“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我想,阿太对黑狗达的教育与《孟子·告子下》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不善待皮囊就是要吃苦,修炼皮囊里的那颗心。也许苦难才是磨炼一个人最好的试金石,有的人被苦难淹没败下阵来,而有的人却在苦难中越挫越勇,将皮囊置之不顾,只听从那颗心的声音,披荆斩棘,战无不胜。
李敬泽
李敬泽在《皮囊》书序中把皮囊和心写得通透极了:
皮囊有心。不管这具皮囊是什么质地,它包裹着一颗心。皮囊可以不相信心,可以把心忘掉。但一颗活着、醒着、亮着的心无法拒绝皮囊。死掉的、睡着不起的心,皮囊就仅仅是皮囊。心醒着的时候,就把皮囊从内部照亮。荒野中就有了许多灯笼,灯和灯由此辨认,心和心、人和人由此辨认。
认识自己就要认识自己那颗心,通过认识自己的他人彼此辨认,同频的人兜兜转转总会遇到,一路前行,一定不是凭借包裹在那颗心之外的皮囊,千姿百态的皮囊也迷惑不了皮囊里的那颗心。
皮囊是有生命限度的,它的生命周期与在这世间的生存长度相关,而皮囊里的那颗心却在岁月里不断强大,挣扎着、等待着、召唤着.......
母亲“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不断鼓励着自己和他人,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毫不客气地反击。生活的压力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坚韧,她鼓励儿子在最该需要拼搏的时期不要放弃努力,去外面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她在丈夫中风后执意要建一座自己的房子,不惜全家吃一段时间“来路不明”的菜叶,直到建好房子的那一刻,才明白,前两次建房子,为的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是一个女人对心爱男人的一种交待。“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
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蔡崇达在《皮囊》中写到了许多与他相关的人,这些人都在不同时期影响着他,而这些皮囊里的那颗心让他看到了这世间的纷繁。
香港的阿小&老家的阿小
黑狗达认识的二个阿小,老家的阿小在小镇上娶妻生子,皮囊与心都固守在一个小地方;香港的阿小穿戴着这个世界最发达地区的东西,肉身却不得不安放于落后似乎有几十年之久的乡下。他对黑狗达说:““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皮囊里的那颗心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皮囊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文展,一个降服了缺陷的孩子
文展是黑狗达迷惑时期走进他的生活,兔唇,有比一般孩子更高的理想,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儿。文展在同龄孩子懵懂的时候就开始整理国家发生过的他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分析发生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他对黑狗达说:“你得想好自己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细化到一步步做具体规划。不过,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这么有清晰人生规划的文展,考上了中专,但在大城市里成长得并不好,因为兔唇遭遇周围人的嘲笑,加上之前故乡造就优越感的落差让他自卑,他开始越厌恶排斥自己的出身,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理想的宏图伟志,但因不太完美的皮囊扭曲了皮囊里的那颗心,道路越走越窄,最终并没有凭借执念向世界证明自己。
皮囊里的心,才是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所在,那些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注定无处安身。
厚朴的理想主义
厚朴是蔡崇达大学的同学舍友,这个理想主义男孩有着青春的冲动,厚朴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在毫无经验的前提下组建乐队,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一味地直白地向世界表示热爱,简单得如同他名字的发音如英文的“HOPE”
蔡崇达总结的是:厚朴确实在用生命追求一种想象,可能是追索得太用力了,那种来自他生命的最简单的情感确实很容易感染人,然后有人也跟着相信了,所以厚朴成了他想象的那个世界的代言人。
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客观且冷酷,它自有一套评判事物的标准,每个人来到这世间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都渴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有时候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处理好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皮囊行走在这世间的必修课,成功的皮囊里都有一颗清醒的心。
人生,就是一具皮囊包裹一颗心的羁旅,在这段旅途中,努力去“看见”,看见皮囊,看见皮囊里的那颗心,看见他人,看见他人看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