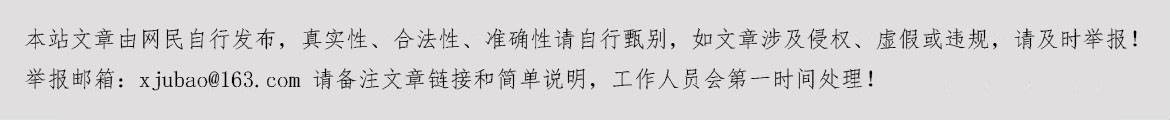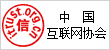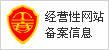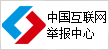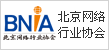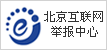程水金教授:我为何给《尚书》做注释?
2021-05-20 21:17:01
《尚书释读》,程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
【后 记】
给《尚书》做注释,并不是我眼下的当务之急。其一,先前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老庄韩思想演进及其观念表达研究》,至今尚未完成结项。其二,本人计划中的多卷本学术专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共有五卷若干册,目前也仅写完三卷五册,还有两卷若干册至今没有动笔。可见本人专长在思想史、学术史的研述,而文献整理或者经典注释,并不是我的强项。虽然在先秦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也时常产生根据我自己的一己之见重注某些经典如《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子书的学术冲动,但都被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推迫着继续前行,不愿停下来再做文本注释以重复过去的工作。然而,之所以搁下手头应当及时完成的研究项目,中断急需继续勉力的专著撰写,而花费三年有余的时间来做《尚书释读》,实在是风云际会,机缘巧合的结果;其间也有顺势而为,也有不得不为的现实诉求。俗话说“计划不如变化”,大抵就是如此罢!
之所以做《尚书释读》,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时间支配自由度受到较大限制。2015年2月28日,我的小女儿程鸣谦出生了。一个已有两个儿子的父亲,又于垂老之际喜添幼女,其快乐愉悦之情,自是不胜言表。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也使我的学术工作与家庭生活发生了时间缠绕。没有任何援手,衹好百事亲为。因此,我既没有大块闲暇精心于学术沉思,也没有完整时空专注于大部头的学术写作。于是想到注释一部经典,逐字逐句的推敲与解读,可以在操持家政与照料女儿的空隙之中,将零散与点滴的时间碎片加以充分整合与利用,故而其写作过程不妨零散化、碎片化,但最终的实际效果却可能是集腋成裘、聚散为整。
工作方向既已调整,只待某部经典的具体确定了。
南昌大学国学实验班的课程设计,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元典精读为主体。本人为国学诸生开设的课程,除却《国学通论》之外,还有《老子》《庄子》和《尚书》。《老》《庄》二书,拙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皆有专门论述,文本解读中的某些个人新见,如《老子》“道,何道也?非恒道也;名,何名也?非恒名也”之读法、《庄子》“天籁”的比喻意义等,以及由此而对老庄思想体系的重新论定,在拙着中已多所揭橥。而且如前所述,本人不大愿意重复已经做过的工作,因此,《老子》和《庄子》自然不会成为我当前的首选,于是我把目光锁定在《尚书》。
说实话,最初给国学诸生开讲《尚书》,也并没有要做一部《尚书》新注本的想法。其原因有二:第一,我的《尚书》课,主要教学目标是引导诸生通读孔颖达的《尚书正义》,通过注疏以及注疏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了解《尚书》学史的相关知识;第二,在经学时代,《尚书》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儒学政典,历代经学家皓首穷一经,尤其是近人顾颉刚、刘起釪师徒二人,更是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与整理《尚书》,想必已经賸义无多。因此,对于《尚书》原文的阅读与理解,只要选取一个好的注本以及推荐几部重要的参考书,让诸生自行阅读也就足够了,用不着我自己专门作注。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这三点理由,都有问题:第一,读注疏的目的,在于理解原典的文本意义,判断注疏的是非,也必须以原典为根基。原典读不懂、读不通,注疏的是与非,也就无从决断;第二,各家经注,众说纷纭而无所折衷者,不在少数;互相冲突乃至自相矛盾之处,亦所在多有。如何判断取舍,对初学者而言,是经典阅读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三,顾颉刚、刘起釪师徒署名合作的《尚书校释译论》,虽然是近代以来《尚书》学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尚书》整理上古史的学术诉求,常常使他们对前人的经注成果失于抉择,甚至有时还不无作法自弊的困挠。例如,援引甲骨文所谓“四方风名”的研究成果,以解释《尧典》“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之四时民生样态,就是明显的败笔。此外,在章句训诂上,尚有不少不通不透之处;在经义阐释上,也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解。所有这些,对于初学者来说,皆弊大于利。因此,出于回归儒家政学经典文本自身的学术诉求,重新整理注释《尚书》,实在是时代学术之需,国学诸生之需。
考虑到国学诸生的阅读水平与取舍能力,我确立了本书注释的基本体例,这就是《凡例》第五条所说的“以【解题】、【释读】、【后案】设其体”。而【释读】部分实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字逐句作文本串讲,二是将原文籀绎成现代语体。串讲部分,既有文字音韵训诂的讲解,也有章法句段及其修辞的解析。至于绎文部分,则曲体文情,以意逆志,不作僵硬的文字对译。串讲部分若有不明彻不通透之处,则可参读绎文以体察经义。两者互相参照,以求对原文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为了便于阅读,在书稿的最后修订过程中,我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博士的建议,将每段绎文之前加上了【绎文】二字,以期醒目之效)。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对经文的处理,力求做到二点:
第一,注重文本的整体性。《尚书》的每一篇文章,虽然其成书年代并不相同,也不出自一人之手,但各自具有自完自足的言说体系。这个自完自足的言说体系,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前后有照应,上下有关联,在遣词造句上具有相关互足的自我诠解性。因此,很多文句,孤立地看,似乎训诂有根据,句义也说得通;但是,将这种解释放在前后句段与文章整体之中考察,则往往驴唇不对马嘴,捍格难通。例如,《臯陶谟》中“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一段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将“挞”字解释为“乡饮酒,罚不敬,挞其背。”并且引用了孔壁古文的不同写法:“���,古文挞。《周书》曰:���以记之。”但许君衹是引古文《尚书》说明“挞”字的古文异体别构,并不是说“挞以记之”之“挞”,就是“乡饮酒,罚不敬,挞其背”的“挞罚”之义。如依许君之说,解“挞以记之”为“挞罚不敬以记之”,则显与上文“钦四邻”之“钦敬尊重”义自相矛盾,而且也与整个文章讲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不相侔。又如《尧典》“畴咨若予采”、“庸命巽朕位”以及“三载汝陟帝位”等等,经注家之所以不得要领,皆因没有联系全篇“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官吏考评制度为说,所以皆不能得其正解。因此,本《释读》在文字训释上,不以辞害志,在选择训诂义项时,尽量考虑具体语境及其上下文意乃至与全篇主旨的关联性,不以单文只字孤立生解。
第二,不放过每一个虚词。自高邮王氏父子倡言“语辞无义”,且认为《尚书》中诸如“诞”、“洪”、“乱”、“迪”等虚词,或为发语词,或为语助词,皆无实际意义。于是后之注经者,多信其说,往往置虚词于不顾。但事实上,《尚书》的每一个虚词,都有非常具体的实际意义及其明确的语法功能。即如王氏指为无义的“诞”、“洪”诸字,都有非常明确的修饰功能。如《大诰》开首“王若曰”一段文字,就是通过“猷”、“洪”、“矧”等几个关键的虚词,将文章联成一气,形成整体,并且暗示着周公更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试看原文:
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厯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引之不明“猷”字的句法功能,认为“猷大诰尔多邦”之“猷”应在“大诰”之下,当作“大诰猷尔多邦”,因辗转传抄而误置于句首。且不仅《大诰》“猷”字如此,《多士》“猷告尔多士”,《多方》“猷告尔四国多方”,均有譌误,“猷”字皆当在“告”字之下。姑且不论三篇文本“猷”字同譌的可能性有多大,仅就“猷”字置于句首而论,乃是修饰整个句段,意为“之所以……,是因为……”。所以,这个置于句首的“猷”字正是一个目的连词,上引《多士》、《多方》两“猷”字,句法功能与此完全相同。此外,“洪”字训“大”,“惟”字训“为”,或训“以”,所谓“洪惟”,实与“降割”之意相关联,修饰“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厯服”全句,强调此乃上天降于周家的更“大”之“割(害)”;从而又与下文“弗……,矧……”这一递进复句相衔接。因此,这一整段文字的意思就是说:
之所以大范围地将你们这些各地方的主要首脑人物以及朝中各位主事大臣召集起来,目的是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向大家通报。最近,无情的老天爷给咱们老姬家降下了不少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似乎没有丝毫的延缓。在这个艰难困厄的时候,最为关键的是,我们继立的君王尚童蒙未开,在本该享受欢乐与幸福的童年时代,便不得不接替这个无比艰巨的历史使命,就不得不承担衹有君主才必须承担的巨大职责。如果他的才华和智慧不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从而引领民衆进入一种和平安宁的生活样态,那就更谈不上能够进一步达到观察天数、理解天命的圣王境界了。
由此可见,正是“猷”字、“洪”字、“惟”字以及“矧”字,将这几个孤立的句段联成一个整体。如果“洪”字没有意义,则“天降割”与“幼冲人嗣无疆大厯服”以及“弗造哲迪民康”云云就失去关联,以致文气散越。而“洪”字所训之“大”,正在与“降割”相比较,以突出强调“最为不堪”、“最不能忍受”、“最为关键”等等如此这般的“言下之意”。而这诸多“言下之意”,却共同指向了一个更加深秘而且也为周公不愿明说的更为重要、更为隐蔽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暗示周公“践阼摄行政当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回应武庚及管蔡“周公不利于孺子”的政治流言。
由此一斑,足见全豹。这些所谓“无义语词”,并非无义。没有它们在各自的句法位置上发挥着各自的句法功能,则文气不能畅达,文意不能连贯,言说者所不便于表达的深衷隐情亦不能轩豁呈露。像这样注重虚词,曲体经义的注释与绎文,本书中所在多有,读者诸君衹要取现行某些《尚书》注释与翻译,进行对照阅读,其是非优劣立可自见,毋庸笔者自衒自儥。
本书撰写的另一个原因是满足国学诸生的教学需要,因而出于教学安排与教学进度的缘故,也使本书呈现某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南昌大学国学班的《尚书》课程每届开设两个学期。第一学期每周两学时,主要用来导读《四库总目〈尚书正义〉提要》、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以及伪孔安国《尚书序》,然后依次读《尧典》、《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益稷》的伪传与孔疏。通过这种方法,使诸生熟悉《尚书》的注疏体例,也借此感受真书与伪书的不同文章风格。这是读《尚书》的基础。第二学期的教学方法则有所改变,以讲授今文《尚书》诸如《盘庚上》、《无逸》、《君奭》、《康诰》、《大诰》、《多士》、《多方》等重点篇目为主,而将注疏的阅读作为预习放在讲授之前。这样一来,我真正需要撰写讲义的就是这第二学期的今文篇目。因此,我首先动手撰写的是《盘庚上篇释读》,依次是《无逸》、《君奭》诸篇。而《尧典》、《臯陶谟》、《禹贡》等《虞夏书》反最后完成。如果通读全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下面两种情况:第一,按本书的篇目排列次序,某些篇目在前的《释读》,在个别文字的训释上,反而指示读者去参考篇目在后的《释读》所引用的例证。虽然在统稿过程中有所修订,但仍然改之不尽,因而也免不了重复。当然,适当保留一些重复,也无非是取便读者,无使前后翻检而已。第二,率先完成的几篇《释读》在行文风格上也与其他篇目不完全一致。依《凡例》第二条所言“前贤旧说,择善而从;否则间下己意,期于经旨之明而已”,最初的撰写,口头讲义的性质比较明显,行文也比较简洁,文字训义,不举例证;对于旧注旧疏以及历代相关解释,也衹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没有更多的辩难与驳正。但在继续撰写之中,却越来越倾向于学术化,繁缛化。例如,《盘庚》上篇《释读》就与中篇和下篇《释读》在行文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在中、后期的撰写过程中,越来越收不住本人难改的积习,不仅“好辩”的不良习气时有流露,甚至有时用语还十分刻薄,丝毫不愿掩饰那种偶有一得便沾沾自喜的狂妄与自大。虽然在最后定稿之前,这类文字有所剔除,但仍然删之未尽。万望读者诸君宽恕我的轻狂,唯谛义是讨,而毋以人废言可也。
最后,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博士以及该社各位同仁,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责任编辑葛云波先生,对拙稿多所劳心。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各位领导对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意。而内子张艺馨教授不仅为本书检覈原文,校读清样,多所劳心;且在山东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之余,又多所劳于承担了大部分生活琐事。其阴阳燮理,琴瑟和谐,夫妻共同奋进之历程,尤当铭以志之。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程水金行甫记于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
【作者简介】
程水金,1957年生,武汉人。文学博士,现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多次负责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重大项目,并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先秦名学文献整理及其思想流别研究》首席专家。撰有《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二、三卷(共五册),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文学、史学及哲学领域皆有较大突破。
【延伸阅读】
不朽的经典文献:略说《尚书》的继承与流传
程水金教授:《尚书》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