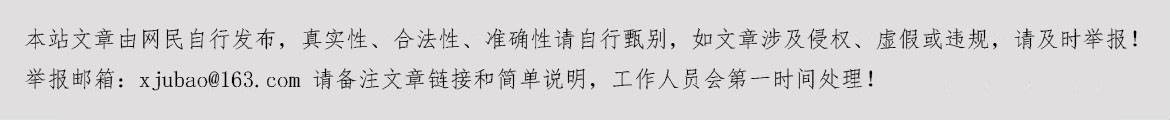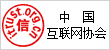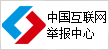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愿意做谁?
2021-06-15 18:15:02
1型糖尿病 http://www.national-tnb.com/yx/
你是否接受自己?你是否想让自己的人生推倒重来?你真的会接受另外一个人生吗?
这个问题出自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本书。这并非一个随意的话题,而是出于对人生沉重的思考。
你是否接受自己?你是否想让自己的人生推倒重来?你真的会接受另外一个人生吗?本期北小河FM,方玄昌、王少华和大河孙来聊聊这些人生的困惑与挣扎。
【本期话题成员】
方玄昌,科普作家,70后
王少华,律师,70后
大河孙,北小河FM主播,80后
【内容概览】
王少华:这还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自己这一生可能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有很多遗憾的地方,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下,你肯定想着我变得不遗憾,而且想做谁,但真选择起来还是有难度。
方玄昌:是的,其实我跟周围很多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因为阿加莎不止一本书用不同的方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她在《死亡约会》这本书里比较直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有过另外的答案的,比方说我曾经想过我想做苏轼或者爱因斯坦,但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比较好。到现在为止,我周围所有聊过的朋友,他们都给出了跟我一样的答案,都是说想做回自己。
大河孙:看某部小说或者是看某部影视剧的时候,人们会希望做英雄或者做什么样的人更好,但实际上随着人生阅历或者见识的增加,总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人,他的某些不足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某些天才可能或者短寿,或者家庭悲惨,或者夫妻关系差,或者父子关系很糟糕,这样的人生你能接受吗?其实那天我跟方老师刚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结论还是做自个儿挺好的。
方玄昌: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给这个问题加一点界定,那就是要做另外一个人,你就要接受他的一切,包括他生活的环境、他生活的时代和他周围所有的整个关系网,还有他的人设以及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你全部都得接受。
人生六个字:慢慢熬,糊涂过。图片:CFP
王少华:会有一些人,如果我有能力做了他,或者说我真有这样的品格,有这么大的能力,我真愿意。我对自己这么不满意,还是要做自己,为什么?因为觉得我的家庭好像替代不来,无法用别的家庭替换这个家庭,我不想选择其他人做父母,我不想选择其他人做妻子,也不想选择别人做我的孩子,这一下就把你限制住了。
我是学法律的,年轻的时候我经常跟别人讲,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欧美法系的出庭律师,因为那时候看很多电影,我喜欢那种在法庭上能够走来走去说服陪审团的场景。我认为在那样的司法制度下,我就有可能展现我的逻辑性、我的能力以及对正义感的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我认为那样很有成就感,很有价值,比我现在做的律师工作更有价值。如果让我人生选择,我真的会那样选择。
方玄昌:我原来曾经考虑做苏轼和爱因斯坦这两个人,最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呢?最主要因素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当前所处的时代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会发现跟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相比,很有可能当前还是最好的。
你更全面地去分析的时候,很容易得出结论,更好的时代应该是在未来。如果认真去思考,一定是这个结果。哪怕是爱因斯坦,他对我们所生活世界的认识也远没有达到今天这么深刻,这么明晰。
大河孙:我有个解决方案,克隆一个你自己。比如说你是1973年生人,你从今天克隆一个自己,生物学上是完全一样的,他就比你晚了40多年,你可以看得到他长成什么样,他怎么克服身边的困难,怎么去施展自己的能力,到40多岁的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至少说已经极度接近于你在未来的那种假设。
方玄昌:其实很不接近,当然这是一个科学话题了。基因能够决定你的先天因素,但他能不能拥有我这个体格还真未必。因为我小时候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迫使我去干那么多活,导致我身体会更强壮一些,而我的克隆体很有可能营养比我更好,他有可能会长得比我更高大,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但他显然不是现在的我,还是会差别很大的,他不会拥有今天我这样的意识,依然是另外一个人。
我们提出了一个纯粹的假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引领之下,我们可能会重新去思考,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我。
大河孙:我们之前讨论过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生个孩子呢?我在处理父子关系的时候,更多看到了我是怎么成长过来的。因为孩子在生长过程中跟父母的各种关系映射到了过去我跟我父亲的互动过程,也帮助我理解最终我是如何长成这样的。
同样这个情况套用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你养育一个孩子,他至少携带了你一半的基因,他好多秉性会让你看到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东西,那是一种共振的奇妙感觉。
方玄昌:我曾经说过,孩子是你生命的一种延续,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这样想,但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王少华:我一辈子做的是法律工作,我的人生标签就是律师,这是我重要的人生标签。我希望换一个人生,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某种理想的实现,到这个年龄才知道人生最重要是体验。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是顺应社会,怎么能习惯社会规则,能够被社会接纳。现在我可能更欣赏改造社会的观念,如同我的另一个偶像马斯克所做的。
这是我想活成的一个人,是现实的人,不像老方说的是一个未来的人。他比我年纪小一点,但是我愿意活成他。他有什么想法他就去实现,我不是说他做的都是对的,谁也不必活成一个完人或者圣人。
为什么我不敢做爱因斯坦,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人,地球上就那么一个天才,那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但是做成一个马斯克那样的,我觉得只要你努力,或者说在某个环境下你是有可能的。
大河孙:为什么选马斯克?是因为他想做就去做了的品性你现在不具备吗?
王少华:对。条件也不具备,品性能力不具备。
在一个自由度比较宽的家庭、地区或者国家,又具备经济条件,智商能力也达到了,他就能做到。比如说像比尔盖茨他们这些人上哈佛、耶鲁照样能退学去做,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行。
你可能也有改造社会的勇气,但可能没有能力去做,或者没有这样的氛围去做。举个简单例子,中国法庭不允许律师在庭上给陪审团来陈词,我们没有陪审团。我做律师不久,有一次开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自动化的控制问题,我可能是看英美的法律片看多了,就举手请示审判长,问他能不能让我站起来讲话,我认为坐着讲话影响我的思维活跃程度。我只是想站起来讲话,还不是电影里的走来走去。然而法官说,王律师请你坐下。
我觉得律师是讲道理的,因为律师做的工作就俩字,就是说服。我希望用声情并茂的方式,用逻辑的方式,最终要说服陪审团或法官,但是我坐在那干巴巴地说,我念条文能说服他们吗?我说服不了。
图片:CFP
方玄昌:你选择自己成为那个样子,然后再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现在走到了只差一步,这一步就是环境所决定的。
王少华:有时候也不完全是环境决定的,当然还跟我个人能力有关,比如说我英语学得好一点,能早一点去留学,我就可以留在欧美做律师。如果纯属环境不满意,我觉得还罢了,我这人就是喜欢更多的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还是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变成别人,变成一个别的人生。
方玄昌:极端案例应该是一些残疾人,就是先天的残疾,他愿不愿意做当前的自己?一开始对于这个话题,我的答案是绝大多数的残疾人很有可能不愿意选择做自己,但后来我进一步去思考,也许我的答案是一种偏见。至少像霍金、纳什这样的残疾人,十有八九他还是愿意做当前的自己。霍金临死之前,你如果问他这一辈子想成为谁,他很有可能会告诉你,我就是想做霍金。其他的那些残疾人会不会这样认为?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有可能需要开放一点。
对霍金来说,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这种疾病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霍金。没有这种疾病,他那本《时间简史》很可能没有那么有名。
大河孙: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有的人不想做女性了,想变成男性,就像前阵子好莱坞艾略特·佩吉宣称要做男人了。
我想回到以前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你能接受孩子平庸吗?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能接受自己平庸吗?我现在听了你们两位刚才讲的那些,感觉似乎是不太接受自己。
王少华:你说的非常对。我能接受孩子平庸,但如果让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是不大接受自己平庸的,因为你对自己要负责。你接受孩子平庸,只是因为他要过他的人生,你不应该去干预他,你得尊重他的人生选择。
你无论多么严苛地要求自己都没有问题,但不能这么严格要求孩子。我觉得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
方玄昌:对于那些变性人,我认为我们需要对ta有足够的尊重,这是很了不起的。实际上ta就是要做回心目中真正的自己,因为性别意识是与生俱来的,ta一定要排开社会上的观众对ta的要求,而依据自己内心所想来做自己。
至于平庸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愿意接受平庸的自己的,包括我自己。我从一个稳稳妥妥的政府部门的工作辞职出来,一步步走,最后走到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媒体人了,这就是当年不愿意接受命运安排的一种挣扎。我从千岛湖的监测站这么一个薪水也不低、社会地位也还可以、在我家人和周围朋友看来都是很完美的一份工作中辞职出来,就是这个原因。我在23岁的时候接受这份工作,但我已经大致能看到顺着这份工作下去,60岁左右我是怎么一个样子,这样的人生我是不愿意过的,我还是想有一些变化。
大河孙:我感觉是你不接受平庸的自己或者对自己现状不满意,这正说明还保持一些年轻的劲儿。因为人越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还可能做很多事情。随着大学毕业,学了某个专业,你总要找跟专业有关的一些工作,即使你转行了,转行的空间也是在缩小的,随着人生不断往前走,可能性在缩小,等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没有可能了。
方玄昌:这也是我说的,当前我还不愿意去成为另外一个人,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我还有未来。我如果成了苏轼,他的这一辈子包括后人对他的评价都已经是一个定数了。而我现在已经年纪接近半百,自己的半辈子已经过去,即使是这样,我还有一个未来,未来是有不确定因素的,这个未知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这个问题分享给围棋手李喆。他思考过之后,给出了跟我一样的结论,他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历史上他所尊重崇拜的那些哲学家,是因为那些人都已经定型了,而李喆还有未知的未来。
反过来,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他已经面临死亡,已经没有未来,它的人生已经定型了,可能剩下只有几秒钟的生命了,这个时候他会给出另外一种答案吗?也不好说。相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弥留之际,对自己过去的这一生肯定会有诸多的遗憾,诸多的不足,诸多的不满,即使这样,他很有可能还是会接受曾经奋斗过、也曾经努力过、彷徨过、痛苦过也精彩过的自己。
王少华:我想象中的自己应该是那样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值得去经历一次,但是我觉得经历的太少了。我觉得可以大胆、开放一点,去想象一下自己,甚至说,如果你重新选择一次,你愿意做个女人吗?我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已经做过一次男人了,体验越多就越值。甚至我们可以问问,你愿意做一头猪或一棵树吗?
方玄昌:之前有人跟我讨论过这种选择。我很喜欢那种特别高大的树,尤其活了好几千年的树,它们见证了人类整个的文明史。愿不愿意做这么一棵树,是有人问过我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做的,可惜的是树没有意识。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所有的假设都是另一种选择没有替代你的意识,你始终是抱着自己当前已有的意识来思考另外一种人生。
大河孙: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比如说把爱因斯坦的意识移植到你现在身上,这不就实现了吗?
2018年12月13日,观众在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博览会(广州)现场与作品《思想者》合影。图片:CFP
方玄昌:这个题目我倒没看到过。不过我还考虑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网络上很多人都说做人要像王思聪那样就好了,一出生就是巨富,有花不完的钱等等。但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让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做王思聪,还不如做一个乞丐,我觉得做个乞丐这个体验也比做王思聪有意思。
因为做王思聪会怎么样,我大概是能想象出来的,而作为乞丐会是怎么一个体验,有一些地方我确实想象不出来,并且我想如果有这么一番经历,它是有价值的。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去尝试着在记者生涯里体会一下民工的生活,原计划是要体会1到3个月,最后是短短一周就结束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而且当时是在上海,工地上太热了。但我认为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在我人生记忆中还是珍贵的。让我去做王思聪我是肯定不干的。
大河孙:第一次高考毕业后,我剃了个光头,还跟我们村民一块出去干了半天民工,就是扛了锄头去修公路。干了半天我就跑了,跑到石家庄市里想看看大城市是怎样的。那时候修公路就要搬石头,要挖路,在那半天的时间里,我就想我究竟是在干嘛呢?十几岁刚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人生的质问。
带着这样的问号,我就反思当年考取的临床医学专业,我以后要做一个医生吗?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我想我还是不能学医学,还是再考一次,就去复读了。
方玄昌:我觉得孙滔这个案例是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你在第一次高考考了一个普通本科不甘心,而要背负第二次高考的压力,包括家庭的经济压力来做第二次选择,这也是不甘于平庸的一个表现。
大河孙: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一个变形,对吧?我给了自己一个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当然选择不是一锤定音的,而是尽自己可能争取更想要的一种人生。
王少华:你们在聊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几个词来体现我的人生价值。第一是好奇。我喜欢对未知的东西好奇,你不想成为一个过去的人,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好奇的东西了。第二是体验。我经历过,我亲身体验过。第三是思考,就是说我体验过了,我还做了深入思考,我还得出了结论,得出了我个人的判断,哪怕判断错了。第四是影响或者叫价值,就是说我对别人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对照这4个词去回忆自己的半生,我觉得还是有挺大的遗憾。比如说好奇,我过去不是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我求知欲不太强,这就是我为什么学文科,因为学理工科你得有好奇心或者有很大的能力。现在50多岁了,好奇心反而比年轻时候还要多一点。
第二,体验。可能相对于我自己很小的圈子,我觉得体验已经不错了,可能超过很多人。但是跟我想象的人生几十年相比,我的体验差得远,当然我现在还在世,我还有机会去体验。
包括思考,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也喜欢反思的人,但你思考出来的东西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结论,或者说至少看不出有多大的社会价值。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影响,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愿意换成马斯克,我认为他对人类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它比那些什么政治家的影响可能还要大。他可能真的能把人类送上火星去生活,这对整个人类来说影响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方玄昌:上火星一定就是像马斯克这样的一群人一块来完成的,马斯克只是其中比较亮眼的一个。我们说体验的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的更多的是前不久的甘肃白银那些户外越野跑爱好者,有一些是职业的,有一些是业余的,有21个人在这场体验中死掉了。
每次户外其实如同一次短的人生,我有的时候是有这个感觉的,尤其是那种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中,比如在小五台遭遇雷击。这种户外体验跟人生确实非常像,因为它前面有无穷的未知,而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未知,最大的风险也在于这个未知。甘肃这一次没有把风险因素给排除掉,那么最后这个未知就成了一个悲剧的因素,但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户外寻找的就是一种未知。
而像王思聪这些人可能就始终是在一种春暖花开的环境里面漫步,你更愿意选择哪一种?我不愿意选择始终是春暖花开、波澜不惊的一种旅途,而愿意选择的哪怕是沙漠、戈壁滩等需要付出艰辛才能到一个高点、要经历一番波折的旅途。像小五台这样,前面有着一些危险在等着你,经过危险之后,你看到了无边的晚霞,一种不可思议的如同《指环王》里面魔多那只眼睛一样的落日。
大河孙:不过我们有时候别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因为我们不是王思聪,说不定他自己也在挣扎,在探索自己的边界。
方玄昌:我说的王思聪是网友眼中的王思聪,真实的王思聪可能是完全另外一种人生体验。
大河孙:王律的“1234”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我刚才就想自己过了30多年不到40年的人生,如果按照你的理论,我追求更多的是可能性。中考的时候,我先是报了个中等师范学校,将来是教小学的,那个时候考上中师也是不错的,很多学生是考不上的,当时我没有犹豫就报了,因为家庭条件很差,想早点工作。但是报了之后,因为班上比较好的同学都报了高中,甚至有同学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一想这个是很糟糕的,别人都去考大学了,我将来要在小学教一辈子,不甘心,然后放弃了中师去读了高中。
刚才说过了,第一次高考后不想一辈子当医生,又放弃医学专业复读考了华中师大。我们好多大学同学做老师去了,我就考了研究生,在实验室待了有一年的时间,感觉按照这个道路,可能就要一辈子在实验室里边呆着了,这又削弱了人生可能性。虽然刚开始还觉得自己要当科学家,但最终明白按照当时的研究环境可能只是做一个工匠,做真正伟大的发明是很难的。于是没读完研究生就工作了。
2008年底开始做记者,2009年就认识方老师了,有好几年干劲十足,直到近几年媒体都不太活跃了,又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是衰退期。在2018年末、2019年初的时候,有几个月特别迷茫,觉得媒体生涯越走越窄,也没有提升的空间,甚至我想是不是回去做老师,起码做老师也是一种体验。最终后来还是去了一个新媒体,然后现在又来做播客。
今天来看,我觉得我的可能性好像又多了一些。因为媒体有衰退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现在有新媒体的发展,视频很火,播客也有抬升的趋势。在以前的媒体生涯里边,记者是不做这些事情的。现在我们做播客像个圆桌式地聊天,至少我们觉得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聊能够聊的话题,能够跟我们比较熟的朋友一块来聊,这是相对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机会来做这个事情,最多去咖啡馆聊一聊,但是他的声音传达不到更多的人。我们有机会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来做,这个机会是很值得珍惜的。感谢我们完美世界给了这么个机会。
从家庭关系来讲,我从我父亲这里也看到了我的命运。他是个文盲,当了一辈子农民,虽然当过兵、入了党,但是现在还是个农民,不会干别的。如果我没有读书,我的命运可能跟他差不多。
王少华:前些年我去户外去探洞攀岩,我父亲非常惊讶,他说儿子你现在做的都是你从小不愿意做、不敢做的事,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呢?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马上50岁了,人生就是体验,再不体验我就没有机会了。
我记得有记者问某个80岁的科学家,说您还有什么遗憾吗?科学家很奇怪:“我现在还活着,没有遗憾,我只能说还有没完成的事儿,只有死了我没完成那才叫遗憾。”
方玄昌:王思聪更像是坐着缆车上山,可以快速到达他的人生顶峰,有天生的优势,而我们更像是徒步爬山,还是重装。
但有些地方他坐在缆车是去不了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这种艰辛努力的过程,在他那里恐怕真的很难体会到。他的人生我认为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体会不到在这些徒步路程中的背包客和驴友的人生乐趣。
王少华:刚才孙滔提到克隆自己,那么你愿意让自己给自己的克隆当父亲吗?
方玄昌:这个可能跟今天主题离得有点远,但我不妨说一说这个事,就是对自己父母亲的看法。我父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在他们去世之前,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常常会思考跟他们的相处,我们也会有一些矛盾,到最后结论都是我错了。对我们兄弟姐妹这7个人的抚养和教育,我的父母亲在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之下,我认为已经是做得最好。
大河孙:总的来说我觉得活到现在,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做还没有做,比如说探索我家的故事,因为我很早有一种纪录片情怀,尤其是那些跟我有关的历史的东西。我很想知道父母小时候日子是怎么样的,甚至包括我自己幼时的生活。我在1岁的时候骑了一个大的木头公鸡拍了张照片,然后那照片就丢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遗憾。我就特别想追溯,哪怕是问问长辈我小时候什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给个机会选择人生,我肯定不要现在这样的。我肯定是跟我的父母、跟我的爷爷奶奶、跟我的姥姥姥爷这些人绑定在一起,我就喜欢跟他们绑定在一起,绝对不分开。
王少华:咱们区别还真是挺大的。我可能是一个做事不后悔的人,对过去的事不留恋的人,我不太念旧,做人不研究。我经常讲,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来,只有今天才是生活,我希望把每天过好。
我做人生计划不超过7天,对于月计划,我觉得能活那么长吗,也不见得吧?这不是杞人忧天。
方玄昌:少华长得像一尊佛,释迦牟尼就说人的一辈子其实就在眼前这一刻。
王少华:我希望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的不同,这就是体验派。
通过主动努力求变,比如说原来我头发越变越少,索性剃光头,我觉得也是一种变化。总不想给人一个一成不变的陈旧的印象,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总希望自己还有什么可能性尽力去试试。
大河孙:总的来说,我感觉是相对于你们两位,我更能接受我自己。
王少华:没错,我可能还是对自己存有很大的不满意。我一个朋友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又跟自己较劲了,所谓的较劲就是跟自己的人生较劲,就是要变。
大河孙:这是不是跟你以前的理论有冲突?以前王律你说改变自己能改变的,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对吧?但你认识到自己的天花板,认识到边界之后,还是要奋争吗?
方玄昌:如果一个人去追求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他就会成为一个野心家,我是不喜欢野心家的。如果未来我还有追求的话,也一定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王少华:实际上我所谓的改变自己是跟自己的惰性做斗争。我父亲为什么对我不满意,说我有10分,我老想着干7、8分就行了,这是我的惰性。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真的判断不了。
方玄昌: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体能的极限在哪,现在我还不清楚,因为我迄今为止,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到这个极点。
其次是,尽管我已经接近50岁了,但未来我还能在其它行业里做出什么东西来,这个也是未知的。所以还是这样,既然未来还没到来,那么就还有改变自己的可能,还能够让自己的未来更精彩。